第一次看到《摄影家的眼睛》这本展览图录是在大阪的摄影图书馆。那是1990年代中期的事了。当时只是从各种资料中看到提及这个重要展览,也开始知道约翰·沙考斯基是个摄影史上不可绕开的重要人物。但一个展览再重要,其展览图录一般不会像图书那样会有固定的入藏渠道。它们更多地被有关学者与美术馆所保存。所以最终看到这本展览图录并不是在图书馆,而是在大阪的一个以会员制方式设立的摄影专业图书馆。当看到这本图录时,内心想到的是,要感谢对于任何事情都有一种狂热的日本人,否则这种容易散佚的图录是较难看到的。今天,这本展览图录已经成为经典并且以图书的方式重新出版,这就有了进入图书馆广为流通并传之后世的可靠保障。更可喜的是,经过唐凌洁女士的介绍,中国的人民邮电出版社要把它译成中文,嘉惠各方摄影爱好者。这个选择是明智的,既证明了这本书的历史价值,也展现了有志于摄影出版的人民邮电出版社的介绍国外摄影经典(不仅是作品意义上的经典,也包括了理论意义上的经典)的诚意。
2006年5月号的《美国艺术》上,发表了马克·杜顿的长篇访谈《大睁双眼:约翰·沙考斯基》。配合这篇访谈,《美国艺术》发表了一张爱德华·斯泰肯与约翰·沙考斯基的合影照片。斯泰肯者,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摄影部主任。沙考斯基者,斯泰肯的后任,从1962年起接替斯泰肯出任MoMA摄影部主任,直到1991年荣退。
这张照片的拍摄日期与拍摄者均不明。照片中,一身标准公司职员打扮的沙考斯基,以典型的美国式潇洒,英气逼人地坐在桌子上,正凝神接听电话。他坐的桌子边上,美髯公斯泰肯将他的左手放在沙考夫斯基的膝盖上,一副神闲气定的样子。画面中,斯泰肯安坐一角,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毫不理会镜头(即画面外的观者)的存在,足以显示他对自己的历史地位有着不容置疑的自信,展现一派功成身退的大家气象。而处于工作状态中的沙考斯基,则属于新手上路,历史地位未定,因而需要人们关注,在照片中与人正面相向,可容观者细细打量。这张照片,之所以值得关注,因为既暗示了斯泰肯的历史地位的不可动摇,也点明了他对于沙考斯基的充分信任。他的左手这么一放,无异于一种加持,交代了权威的传递与传承关系,并赋予正在出现的新权威沙考斯基以合法性。作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张照片有点像那些把毛泽东与华国锋画在一起的《你办事我放心》。不过在这张照片中,斯泰肯与沙考斯基的关系因两人表情、姿势与动作的丰富变化而显出一种美国作派。而如果把这张照片中的精力饱满甚至有点稚气的沙考斯基与十多年后由阿维顿拍摄的疲惫消瘦的同一人比较,可以想见他在这个位置上的付出之大。
的确,沙考斯基没有背叛斯泰肯对他的期待。作为美国摄影的掌门人,他在MoMA摄影部主任任上一路走来,真正将MoMA拉抬至美国摄影甚至一度是世界摄影的龙头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借美国国力强盛之势,强力牵引当代世界摄影的发展。

ohn Szarkowski Succeeds Edward Steichen by Paul Huf
在长达近三十年的“统治”下,沙考斯基策划的一些展览,有些直接影响到了当代影响的走向。他在1967年策划的展览《新纪实》,将阿巴丝、弗里德兰德、维诺格兰德三人的摄影实践概括为“不是为了改革世界,而是为了解世界”,强调了纪实摄影朝向作为一种个人表现样式的转向。同时,此展览也确认此三人的摄影风格具备了一种艺术性,由此赋予纪实摄影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样式的合法性。他于1978年策划的《镜与窗》(1978),则试图从理论上概括摄影作为一种认知世界与表现自我的不同手段的不同特质。而他策划的《埃格尔斯顿的指引》(1976),虽然在展出当年被评为“最差展览”,但现在看来,在彩色摄影几几乎成为当代摄影“主流”的今天,他的眼光不无先见之明。
除了不遗余力地推出美国摄影新人,他还积极策划为一些老摄影家做展览,确认他们的历史地位与艺术成就。兰格、埃文斯、威斯顿、亚当斯、阿维顿、潘恩等美国大师(American Master),都在沙考斯基任上,经过MoMA这个权威艺术机构的展览与传播,从鲜为人知的摄影家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国民性文化人物。沙考斯基将这些人的摄影实践置于美国本土文化实践的脉络中加以展示,在确认了他们的历史地位与贡献的同时,也树立起美国现代摄影的风格与趣味的标本。而从更高层面来看,其实沙考斯基通过自己(当然还有其它方面)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因为二战而出现的、由蜂拥进入美国的欧洲摄影家所形成的某种主导性局面,帮助实现了扶助美国摄影的本土实践的“摄影美国化”目标,建立起一个有迹可循的美国摄影传统的谱系。“摄影美国化”,尽管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人明确提出过的、更不会是政府主导的目标,它只是或若隐若现、或始终念兹在兹地闪现于美国本土摄影人内心的精神向往,但在美国的文化实践中,始终是一个梦想与不断实现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沙考斯基是一个实质性地改变了美国摄影的摄影家国籍构成的人,当然,他同时也因大批推出杰出的美国摄影家而改变了世界摄影版图。他在MoMA的三十年时间,正好与世界摄影的重心向美国、向世界城市纽约转移的时刻重合。这种重心转移以及伴随而来的文化主导权的转移,不言而喻,与他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沙考斯基作为一个杰出的展览策划人,为摄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样式进入现代艺术制度,为美国现代主义(American Modernism)摄影的美学在艺术制度内获得合法性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沙考斯基巧妙地将自发的、野生的美国现代主义摄影实践不露痕迹地、从长计议地纳入现代艺术制度框架中,并同时逐渐增强艺术制度对于摄影这个新品种的适应能力。他的这种努力具有双重意义,既要驯化进入制度的摄影的桀傲不逊,也要帮助制度建立与培植对于摄影的信心与热情。当然,这存在着将摄影异化的危险性。但既然摄影“艺术”了,那么它被艺术制度招安也就名正言顺。历史地看,发生于二战间(inter-wars)的欧洲现代主义摄影与先锋摄影,在摄影的语言实验方面,可做的已经告一段落。这样的欧洲式的摄影实验,实质上具有一种反摄影的色彩,但摄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表现,尤其是其表现上的精致性却仍然有待开拓。而沙考斯基通过自己的展览策划实践,给世界摄影史烙上一个不可磨灭的美国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如何使美国摄影实践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承认。而他对于快照风格的高度推崇,更使美国摄影具有了明显不同于其它时期与地区的摄影实践的区域特征。也许,他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将快照风格美学精致化,突出其作为美国摄影实践的本土性。在他的推动下,美国摄影获得了一种美国性的品质。在他上任之时,正好是美国国力强盛,有意塑造文化大国形象的当口,而年轻的媒介摄影正好与当时的超级强权美国的活力相般配,其地位水涨船高,一路扶摇直上。他推出阿巴丝、弗里德兰德、维诺格兰特、埃格尔斯顿等人,既证明了他的眼光,也正得其时。尤其是1970年代,美国式的快照风格影响远及国外。在他手中,由MoMA推崇的摄影,被悄悄地转化成美国文化的象征之一。
作为艺术制度中人,他为摄影的制度化做出了实在的具体贡献。在他就任摄影部主任后第三年,MoMA于1964年开设了永久性的摄影画廊,使人们在美术馆接触摄影艺术作品成为一种惯例,提升了摄影在公众中的认知程度。他通过各种方式筹措资金,扩大MoMA的摄影收藏。到他离开时,MoMA已经拥有超过20000张照片的摄影收藏。沙考斯基也曾经创设了每周定期接待摄影家的做法,让许多年轻摄影家有机会与美术馆接触,展示自己的工作,而他也会适时购买他们的作品,表示一种精神支持与物质性鼓励,并且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机会。像现今已成大师的日本摄影家杉本博司,当他在纽约刚开始职业艺术家之路时,就曾赴MoMA摄影部的定期接待日,因受到沙考斯基的鼓励而大受鼓舞。当然,对于像杉本博司这样的优秀摄影家,沙考斯基决不会吝惜他的预算,他当场就购买了他的《自然史博物馆》系列。而丰富多变的布展方式,不仅将展示手法精致化,也达到了突显摄影这个媒介的特质的目的。他的许多摄影展览,在摄影布展上,给后人留下丰富的遗产。摄影与艺术制度的关系,其实也是需要经过各种各样的展览实践,同时也是展览实验才能获得确认、固定与强化。
沙考斯基的摄影理论思考与他的展览策划活动齐头并进,并通过一系列展览逐渐形成并具体化。他的展览活动丰富了他的摄影理论思维,他的理论思考反过来又体现于展览中。比如,他于1964年策划的《摄影家的眼睛》展览,就尝试以展览的形式,系统地提示摄影批评的手法。此展览图录于1966年出版,成为学习如何观赏摄影的入门宝典。他认为分析照片可从五个方面着手,那就是细节、画面框取、拍摄视点、时机与事物本身。这五个方面实际上与摄影这个视觉媒介本身的媒介特性有关。这对于如何从形式层面判断照片的好坏给出了一个基本路径。当然他也指出不能孤立地用这五个方面来看照片,而是要有机联系地综合观察。他的前同事玛丽雅·莫里斯·汉伯格认为,由于此书的出现,“终于出现了可以谈论‘为什么这张照片如此精彩’的土壤。”可以说,《摄影家的眼睛》为确立现代摄影的美学标准与批评术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展览本身,出现于他刚上任不久,其实也是一份工作宣言与应战。他必须通过这个展览回答人们的悬念,他是如何选择作品与摄影家,他必须通过具体的作品与展览向人们提示自己作为MoMA摄影部的新掌门人的美学标准与鉴赏能力。
沙考斯基曾经说,“《摄影家的眼睛》是一种尝试,试图定义某些议题,某些基础性的议题,开始给摄影爱好者以一种可靠的词汇,那与摄影切实相关,而与斯蒂格里茨如何感觉大烟囱或其它什么的事情无关。”尽管这只是一个就摄影论摄影的评判方式,并没有将摄影置于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脉络中加以考察,但确实奠定了形式主义摄影批评的基础。而这也是引向更深入的摄影批评的必经之路。而作为一种阅读照片的基本训练,这本书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今天的摄影批评者,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者多,因此,此书不失为一本基本的补课教材。
不过,他曾经在访谈中回应人们对于他的形式主义批评的评论时说,“那只说对了一半”。他说:“我对于作为一种制像系统的摄影感兴趣,而那是一个形式议题,但在我最为赞赏的摄影中,画面结构已经深入地包埋在图像中,以致于不可能把这两者分开来考虑。”而他的另一本受到广泛阅读的摄影批评著作是《看照片》,那书以更大众化的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他选择了100张照片(当然都是来自MoMA的收藏品),对于每张照片都有一页文字加以点评,不着痕迹地将他的摄影美学观传播给大众。1990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曾经这么说:“沙考夫斯基的想法,无论美国人知道还是不知道,已经成为我们对于摄影的想法。”无论幸与不幸,沙考夫斯基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其社会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1929年开张的MoMA,于1930年获得第一张摄影收藏品。那是埃文斯的一件摄影作品。1940年,MoMA正式成立摄影部,由摄影史家弗蒙特·纽霍出任首位主任。他于1946年因为内部争斗而黯然离开MoMA。纽霍的遗缺由摄影强人斯泰肯接任直至他1962年退下。在沙考斯基之后,则是至今仍然在任的彼得·格拉西。如果说纽霍为摄影在现代艺术制度中获得一席之地出了大力的话,那么斯泰肯将摄影作为一种见证手段全力推广,获得了广泛的公众认知,而他本人也因MoMA这个大舞台面而出尽风头。而到了沙考斯基任上,则是稳步扩展摄影的影响,使之最终跻身于现代艺术之列。是沙考斯基的努力,完成了在现代艺术制度框架内将摄影学术化、精英化的历史任务。摄影这个野孩子被艺术制度回收招安之功,可能是沙翁对于摄影的最大贡献。有人说他在MoMA 的近30年,“一手推动将摄影视为自足的艺术形式的形式主义理解”(Erina Duganne),诚非虚言。沙考斯基对于摄影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但在他任上后期,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对于摄影开始产生影响,而他的反应有点迟钝。他过于强调摄影的纯粹性,因而较难以更为开放的心态接受对于摄影的各种侵犯与挑战。也因此,他的影响开始衰退。他于1989年策划的《至今为止的摄影》,是一个纪念摄影术发明150周年的大型展览,也可说是他任上最后一个重要展览,但他却是从摄影技术的发展来呈现摄影表现的变化,由此可以感受到他对于应对当时现实的意愿缺失或有意回避。两年后,他从MoMA摄影部主任任上荣退。不过,这反而证明,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不会因时势变迁而改变自己的标准。
沙考斯基1925年出生于威斯康辛州阿什兰的一个波兰移民家庭。他在11岁时就开始玩耍照相机。那是他父母给他的礼物。在16岁上,他已经开始其职业摄影的生涯。不过他同时考入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主修艺术史,并于1948年取得学位。他认为要从事摄影,学习艺术史总是没有坏处。在大学求学期间,他曾经于1945年到1946年间加入将美军服役两年,身上沾染了些许二战的征尘。大学毕业后,他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沃克艺术中心担任专职摄影师。1951年到1953年,他在纽约州布法罗的阿尔布莱特艺术学院教授艺术史与摄影。而后,他成为自由摄影师直到接替斯泰肯出任MoMA摄影部主任,并“统治”摄影部长达29年。他曾经两次获得过古根海姆奖金。他的经历与“成功故事”,其实也是令许多人艳羡不已的美国梦的美谈之一。
2005年2月5日到5月15日,一个名为《约翰·沙考斯基:照片》的展览在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此展览由约翰·沙考斯基的传人,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高级策展人桑屈拉·菲里普斯所策划。其实,这个曾经一言九鼎、一度主宰当代摄影走向的美国摄影掌门人,作为一个有着摄影实践“前科”,并且顽固坚持自己的独特美学主张的摄影策展人,一直不曾忘怀自己的摄影创作。只是他的摄影创作长期以来一直因为“瓜田李下”的原因而鲜为人知。此次展览,揭开了笼罩在沙考斯基身上的面纱,将他此前秘不示人的摄影作品做了一个回顾性质的展示。通过这个展览,人们全面了解到沙考斯基的摄影趣味。至少人们可以了解到,他自己的摄影美学观与他所策划的大量展览其实是相当地统一,尽管他有自己的趣味局限,而且这种局限也可能影响了他的策展。人们以前只是通过他的展览了解他的摄影观,而这次,人们有机会通过他自己的摄影作品,了解他的摄影美学观与他的摄影策展实践的关系。2006年2月到4月,此展巡回到纽约MoMA。沙考斯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回家“探亲”。与此同时,他还在纽约的佩斯/麦吉尔画廊举办了《沙考斯基的现在》展。2007年7月7日,他在麻省匹兹菲尔德去世,享年81岁。
再次感谢唐凌洁女士优美精准的译文,让我们充分领略沙考斯基的摄影观,同时也要感谢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此书。这是对于中国摄影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有益贡献。 本文转载自:www.rayartcenter.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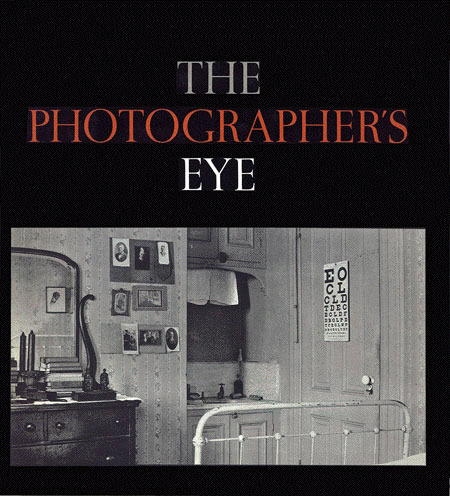





































有什么想法跟大家交流下吧~